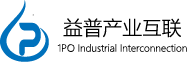美国发布《美国优先贸易政策》总统令
2025年1月20日,特朗普政府签署《美国优先贸易政策》总统令,其核心目标是重构美国贸易规则以缩减贸易逆差、增强国家安全并保护国内产业。该政策以国家安全为名,行经济竞争之实,标志着美国贸易政策向“新重商主义”的彻底转向。
一、政策详细解读
(一)政策背景与核心目标(Section 1)
该政策明确延续2017年“美国优先”贸易政策框架,强调将贸易政策与国家安全、国内产业振兴深度绑定。其核心目标包括:
重构贸易规则:以缩减贸易逆差为核心抓手,通过关税、产业保护、技术封锁等手段重塑全球供应链,降低对外依赖。
国家安全优先:将贸易政策工具化,直接服务于关键产业(如半导体、新能源)的自主可控,防范“战略竞争对手”(如中国)的技术渗透。
国内利益群体保护:以工人、农民、制造商等传统产业群体为政治基础,通过强化反倾销、政府采购本土化等措施巩固选民支持。
法律依据:引用美国法典(如15 U.S.C. §71-75、19 U.S.C. §2411等),依托既有法律框架赋予行政机构广泛的调查与执行权,规避立法程序对政策实施的掣肘。
(二)对“不公平贸易”的系统性打击(Section 2)
本节为核心操作模块,通过12项条款构建全方位贸易壁垒:
1、全球补充关税(Section 2(a))
美商务部主导调查贸易逆差成因,提出“全球补充关税”建议。该关税可能针对特定国家或商品类别(如钢铁、电子产品),税率动态调整以平衡逆差。突破WTO最惠国待遇原则,引发连锁报复。例如,若美国对墨西哥汽车零部件加征关税,可能迫使车企将供应链转移至非关税同盟国。
2、对外税务局(ERS)的设立(Section 2(b))
整合海关与边境保护局(CBP)职能,强化关税征收能力,重点打击小额免税包裹(de minimis)滥用(如中国跨境电商利用800美元以下免税政策)。可能引入区块链追踪货物原产地,或要求电商平台预缴关税保证金。
3、反倾销与反补贴(AD/CVD)规则收紧(Section 2(h))
关键调整:
“归零法”(Zeroing)复活:在计算倾销幅度时忽略出口价格高于正常价值的部分,人为提高税率。
跨国补贴认定:将中国对第三国(如东南亚)企业的补贴视为间接损害美国产业,扩大制裁范围。
案例:若中国光伏企业通过越南转口,美国可能追溯其在中国接受的补贴,并对越南出口组件征收惩罚性关税。
4、USMCA重新谈判铺垫(Section 2(d))
审查重点:
原产地规则升级:要求汽车零部件北美本土化比例从75%提高至90%,并纳入电池、芯片等敏感品类的“原产地+技术标准”双重要求。
劳工条款工具化:以墨西哥劳工权益不达标为由,限制其出口配额,变相推动制造业回流美国。
5、汇率操纵国认定(Section 2(e))
标准扩展:除传统贸易顺差、外汇干预指标外,可能新增“数字人民币跨境支付系统(CIPS)对美元地位的威胁”作为评估因素,为制裁中国提供借口。
(三)对华经贸关系的全面施压(Section 3)
1、中美第一阶段协议执行审查(Section 3(a))
该命令要求美国贸易代表审查美国政府与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之间的经济贸易协定,以确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是否按照本协定行事,并应根据本次审查的结果建议采取适当行动,直至并包括根据需要征收关税或其他措施。
焦点领域:农产品采购量、金融开放进度、知识产权刑事处罚案例。若认定中国未履约,可能重启对约3700亿美元中国商品的关税(目前部分被法院暂停)。
2、技术脱钩深化(Section 3(b)-(c))
该命令要求美国贸易代表评估2024年5月14日题为“对第301条调查所采取的行动的四年审查:中国与技术转让、知识产权和创新有关的行为、政策和做法”的报告,并根据《美国法典》第19篇第2411条的需要考虑可能的额外关税修改——特别是在工业供应链和通过第三国规避方面,包括对此类审查中发现的任何不公平贸易做法所造成的成本的最新估计——并建议采取必要的行动,以纠正与这一进程有关的任何问题。
供应链审查:针对中国通过马来西亚、墨西哥等第三国规避半导体出口管制的行为,可能要求这些国家采用美国技术占比标准(类似“实体清单”域外适用)。
新兴技术封锁:将人工智能、量子计算纳入出口管制,援引《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IEEPA)限制美资VC对中国科技企业的投资。
3、知识产权对等(Section 3(e))
该命令要求商务部长评估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人的专利、版权和商标等美国知识产权的状况,并应提出建议,以确保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对等和平衡地对待知识产权。
潜在措施:要求中国取消“强制技术转让”相关法规(如《外商投资法》中的本地化条款)。对中国在美专利实施“安全审查”,以国家安全为由撤销敏感技术专利(如5G、生物医药)。
(四)经济安全与产业保护(Section 4)
1、“232条款”扩大化(Section 4(a)-(b))
产业范围延伸:从钢铁、铝扩展至稀土、制药原料,赋予总统直接限制进口的权力。例如,以“依赖中国稀土威胁国防”为由,要求国防承包商五年内实现稀土供应链去中国化。
2、出口管制体系升级(Section 4(c))
“小院高墙”2.0:
技术清单动态化:建立“受控技术指数”,根据中国技术追赶速度自动更新管制范围。
长臂管辖强化:要求第三国企业使用含美国技术超10%的设备对华出口时需申请许可(当前门槛为25%)。
3、投资审查双向收紧(Section 4(e))
对外投资管控:修订14105号行政令,将人工智能、清洁能源等纳入“受关注技术”,要求美企对华投资需预申报,并设立“负面清单”禁止关键技术外流。
(五)执行机制与权力分配(Section 5-6)
1、跨部门协同架构:
商务部主导产业审查(Section 4(a))、财政部统筹关税改革(Section 2(b))、贸易代表办公室(USTR)聚焦对华施压(Section 3),形成“三位一体”执行体系。
时限压力:要求2025年4月前提交报告,为2026年中期选举前落地政策造势。
2、法律规避设计:
“不创设权利”条款(Section 6(c)):规避司法挑战,确保政策灵活性。例如,企业无法以“违反WTO规则”起诉美国政府,因备忘录明确排除法律追诉权。
(六)政策逻辑与战略意图
经济民族主义制度化:通过行政令将“美国优先”从政治口号转化为常态化政策工具,弱化多边规则约束。
“友岸外包”加速:以关税和政策审查倒逼盟友(如墨西哥、越南)选边站队,构建排除中国的平行供应链。
技术霸权维护:通过出口管制与投资审查,锁定美国在AI、量子计算等领域的代际优势,延缓中国产业升级。
二、对全球贸易的影响
1、贸易保护主义升级与全球供应链重构
政策要求对贸易逆差国实施“全球补充关税”(Global Supplemental Tariff),并可能通过新设“对外税务局”(ERS)强化关税征收。这将加剧美国与主要贸易伙伴(如中国、墨西哥、欧盟)的摩擦,引发报复性关税,导致全球贸易成本上升。例如,美国对墨西哥和加拿大商品威胁征收25%关税,可能破坏USMCA框架下的区域供应链稳定性。
美国对USMCA的2026年审查可能推动重新谈判关键条款(如汽车原产地规则、劳工标准),甚至引入针对中国企业的限制措施(如通过墨西哥转口规避关税),迫使北美供应链进一步“去中国化”。
2、多边贸易体系进一步弱化
政策要求重新评估现有贸易协定(如WTO政府采购协定),以确保优先采购美国产品26。此举可能削弱多边规则约束力,促使其他国家转向双边或区域协定,加速全球贸易体系碎片化。
对“货币操纵国”的审查和制裁(如汇率政策评估)可能激化与日本、韩国等依赖出口的盟友矛盾。
3、新兴领域规则主导权争夺
美国拟收紧对战略技术(如人工智能、半导体)的出口管制,并通过“互联汽车”等规则限制外国技术进入。这可能引发欧盟、中国等技术大国加速自主标准制定,形成技术贸易壁垒。